
【编者按】当语言模型越来越像人类,“意识”这一哲学和科学交界的谜题依旧未解。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科学与哲学的碰撞?今天,我们带来《我的哲学探索》一书中最为深刻的一章,作者试图以哲学的视角、科学的案例、认知的反思,走出现代科学对“意识”的困境,照亮一条从“现代常识理性”迈向“科学理性”乃至“真实性哲学”的道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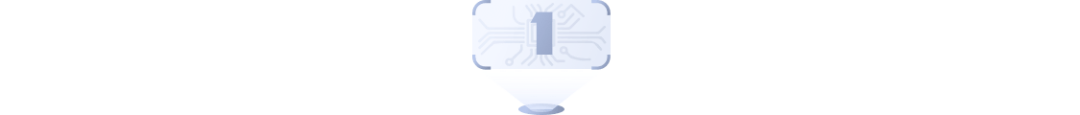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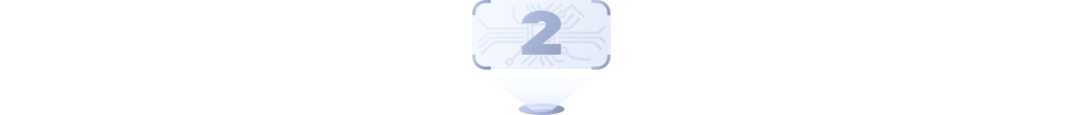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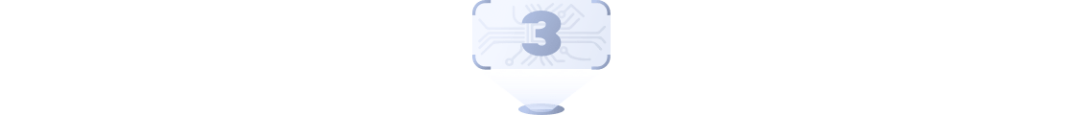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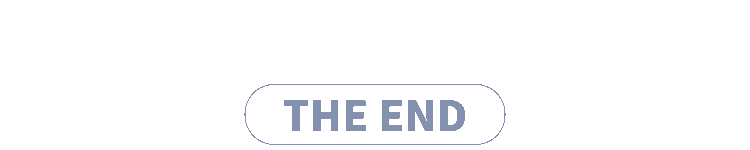
(文:AI科技大本营)


【编者按】当语言模型越来越像人类,“意识”这一哲学和科学交界的谜题依旧未解。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科学与哲学的碰撞?今天,我们带来《我的哲学探索》一书中最为深刻的一章,作者试图以哲学的视角、科学的案例、认知的反思,走出现代科学对“意识”的困境,照亮一条从“现代常识理性”迈向“科学理性”乃至“真实性哲学”的道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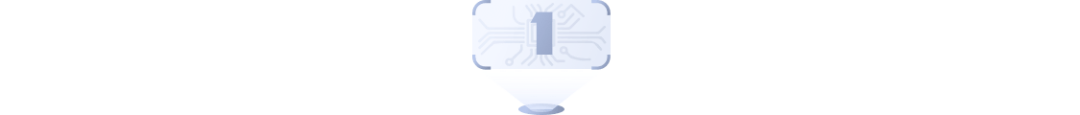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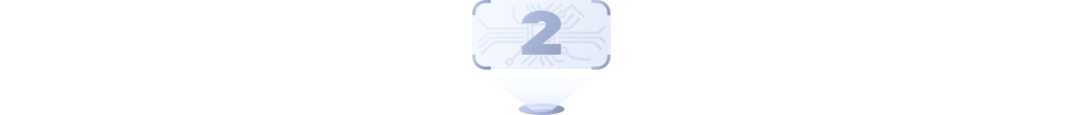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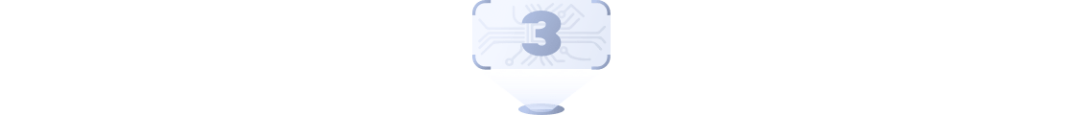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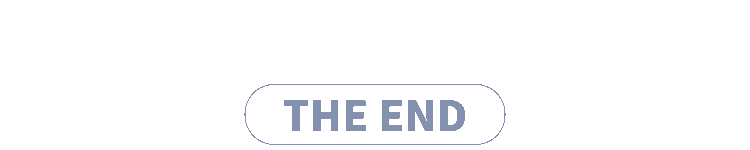
(文:AI科技大本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