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|
机器人的软硬件固定投入,只占价值链条的一两成,后续的部署维护才是最大成本。
|
文|邱晓芬
编辑|苏建勋
若你留心过「逐际动力」这几年在各大展会的露出,或许会对这一幕印象深刻——工作人员和观众们猛然抬腿,一次次踹一台小型双足机器人。机器人在踉踉跄跄中逃窜、又站稳。

当这台机器人成为他们的流量密码时,很多人可能会以为,「逐际动力」便是一家只做机器人腿的公司。这就错了,「逐际动力」的创始人张巍认为,他们更想做的是,“具身智能领域的英伟达”。
确实,放眼如今灼热的具身智能赛道,「逐际动力」的定位很独特。在一众厂商讲大脑的故事,甚至将VLA当做宣传标语时,张巍反而认为,当前具体模型性能不是最重要的。
在他看来,现在大脑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方案,烧钱堆真机数据没有用,从不同数据中提取对操作任务有用信息的能力才是关键——张巍将其称之为,生产具身模型的“工业母机”。
基于这种判断,「逐际动力」更希望通过提供本体、小脑、模型开发工具链,帮助下游客户把大脑做出来。张巍很坦诚表示,“我们没有那个Know-how去进入具体的场景”。因此,「逐际动力」在商业选择上,相比大多数机器人公司像是“后退了一步”。
张巍用三个字母抽象了他们的目标客户画像——“IDS”:Innovator,包括科研院所、科技公司;Developer,开发者,这部分客户主要根据现有技术开发新功能;System Integrator,系统集成商,把已有的技术和功能整合到落地方案中。
通过这三类用户,张巍希望「逐际动力」服务机器人的创新过程,包括技术创新、开发创新、方案创新。

而这种商业判断,主要源于张巍对于机器人落地现状的观察。2025年,落地是悬在大多数机器人厂商头上的剑,大家纷纷在工厂、康养、零售等场景尝试。张巍却认为,让机器人替代人,是一件“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事情”。
在他看来,机器人落地的软硬件固定投入,只占整个价值链条的10%-20%,而后续的部署、维护,才是最大的成本。
不难发现,如今机器人行业落地的常态是,要让一台人形机器人替代掉一个工人,往往要“搭上几个很牛的、算法的博士”,并且,项目接得越多,公司也赔得越多。张巍直言,“机器人落地的最后10%,足够杀死前面的90%。”
8月上旬,《智能涌现》与张巍聊了三个小时。鲜少露面的他,延续了一贯犀利的风格,喜欢传递反共识的观点,也擅长将自己的看法做高度抽象概括。
他分享了对于机器人落地的观察、对机器人形态之争的判断、以及他对于现在大火的机器人大脑的看法。以下是《智能涌现》与张巍的对话实录(略经整理)。
OPEX,机器人最大的幻觉
《智能涌现》:你认为机器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落地,中间的卡点是什么?
张巍:我现在觉得具身机器人已经落地了,星猿哲、梅卡曼德这些都是AI driven的机器人公司,人家在厂里干也干了挺长时间,虽然很苦,但其实已经落地了,他是有大脑的,只是大脑还不够好,但他并不是纯编程的东西,他有感知、有定位、有决策。
《智能涌现》:在您看来,所谓的落地的标准是什么?
张巍:我们自己有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判断。让机器人用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,但你不要觉得它用起来就是落地了,关键是你要花多少精力才能用起来。更难的是,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系统化代替我们人类,去实现效率的提升,成本有没有降下来。
那么,为什么机器人落地难?原因是,大家看到机器人好像代替了一个工人,然后去算机器人的账,计算机器人替代工人大概几年能回本。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。
我觉得在整个价值链条里,机器人代替人,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事情,它只占整个价值链条的10%-20%。用机器人的本体和软件去代替人不难,维护部署机器才是最大的成本。
机器人落地的时候,大家往往关注的是CAPEX(Capital Expenditure,资本性支出),就是固定的投入,忘了其实它的OPEX(Operating Expenditure,经营性支出)是最大的、是很难的。
《智能涌现》:机器人具体的OPEX包括什么?
张巍:对于维护运营这件事需要哪些技术变量,你要有估计和预测,同时你要对这个业务非常了解。
但是现实是,懂业务的人不懂技术,懂技术的人不懂业务,所以这个估计的偏差是很大的,导致大家很容易Underestimate(低估)这件事。
即使机器人落地已经达到90%了,剩下那10%可能要花一年两年,甚至更多的时间。90%听上去已经挺高了,但最后那10%是杀死他的。比如要替掉一个工人,最后发现,还要搭上几个博士才能把他替掉,还是很牛的、懂算法的博士。
我觉得现在的具身大脑,是个很有价值的技术变量,但如果商业模式没有想清楚,落地场景没有搞明白,说要进工厂里用,它连赔钱的资格都还没有,它不是赚钱的开始,是赔钱的开始。
这是上一代机器人的教训,搭这么多钱去维护啊,给自己耗进去。公司接的项目越多,赔的越多,都是这种状态。
和Robotaxi这件事一样,它不是个技术问题,它的商业本质是运营问题,整个商业闭环是需要很多环节的,A B C D E。A再牛,B、C、D、E不成熟也不行。
《智能涌现》: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机器人公司的商业化的动作,并不是像您提到的找到一个那么高要求的场景落地,而是沿途下蛋,这也是现在行业里面的共识吗?
张巍:我觉得这么想的人是有的,但也不是全部。你对你选的场景的整个业务链条,理解要够深,而不是技术理解,要了解技术在每个链条里的成熟度、稀缺性。
我觉得机器人厂商既做A又做B,各个领域都落地,是挺难的,因为最后那一公里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,背后积累的门槛往往甚至比技术的门槛还要高。考验着行业的Know-how、行业里的地位、模型的优势。除非你认为你自身的核心价值就在于,对行业红海的深刻理解。
现在机器人领域能算过来账的场景,基本都被干到红海了,你去工厂里,凡是能自动化的都自动化了,剩下的好像都不是太简单的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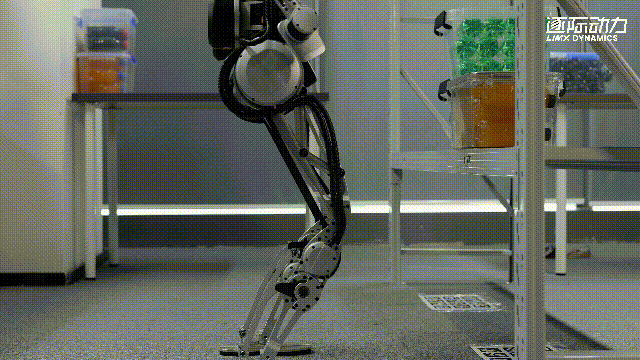
做机器人上半身,不是创造
《智能涌现》:基于这样的商业认知,你们怎么去推进机器人的落地?怎么应对红海的竞争?
张巍:人形机器人目前看不到能立刻落地的应用,长期来讲,他没有太大的效率提升,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形态,是CAPEX的最优解。
因为,任何一个专项的任务,只要任务足够单一、量大,一个通用的机械臂就搞定了。而从机器人诞生的那一天起,从自动化到机器人的变革,就是从专用到通用的一个变化。
从机器人的形态上来讲,我们就觉得就四类机器人:
最简单的是只有胳膊的机械臂;
第二类是,你在展会上看到的90%都是轮式加两手臂的轮式双臂机器人,我称之为轮椅上的人;
第三类是真人形机器人;
第四类是没有上半身只有腿的机器人。
轮式双臂机器人,解决的是平地移动的能力。机器人的“腿”,解决的是地形上的适应能力,从A到B。
《智能涌现》:在形态上你们选择的是后两种,为什么腿那么重要?
张巍:我们谈本体,就要谈小脑和运控。小脑和本体是耦合在一起的,没有什么东西比机器人好做,机器人比车好做多了,但是大家做不出来的原因在于,我能不能很好地控制他。
80年代的工业机器人出来,行业里就产生了传统的工业运控算法,诞生了机器人的四大家族(四大家族为ABB、安川、KUKA、发那科)。
这套算法模型基于动力学、运动学、解算,已经很成熟了,套到轮式双臂上也基本能用,因此,轮式双臂是不需要小脑的AI化的。
我们觉得,轮式双臂机器人和机械臂的形态是个成熟且极其卷的东西,整个技术方案是很成熟的,以前能做,现在也能做,只不过现在有这波风潮了。这不是创造,而是供应链逻辑。
为什么我们选择做腿和人形?因为腿和人形机器人是新的。带腿的人形必须实现小脑AI化,因为有腿需要平衡,AI化能大大缩短整个开发周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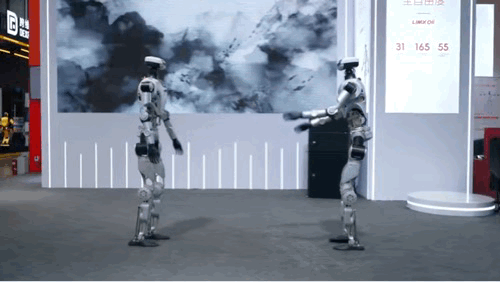
《智能涌现》:小脑有没有AI化,有什么样的差别?
张巍:现在的小脑,无论有没有AI化,它都是基于模型的,只不过人们使用模型的方式上产生了质的变化。
早期机器人四大家族的时候,人们使用模型的方式是通过符号去理解、推导使用模型——人通过对事情的理解,对模型的理解,通过符号的演绎,把控制器设计出来。
到了波士顿动力这一代,模型的使用方式变成从符号变成计算。我需要用一些优化的方式把一个解计算出来。AI化的本质,我觉得就是在仿真器里,用模型产生很多的数据,通过数据来去训练出控制器,这个是它的最本质的变化。
现在的机器人大脑,大家在点状尝试各个场景。人形,是最能发挥大脑价值的一个形态。
《智能涌现》:你们的客户是哪些,都有哪些特点?
张巍:我们把它分成了三部分,IDS——Innovator,这部分包括科研院所、科技公司,主要负责创造新技术;Developer,这部分人不一般不发明新模型,他是根据现有技术,开发新功能;第三部分是System Integrator,整合各种技术和功能,把针对某个应用的方案做出来。
我们不服务终端用户,我们服务的是创新的过程,IDS分别对应的是,技术创新、开发创新、方案创新。我们是具身NVIDIA,模型不是我赚钱的方式。
《智能涌现》:IDS 的这套客户体系是您什么时候思考出来的?
张巍:今年确定下来的吧。
《智能涌现》:我感觉你们的模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,你们的定位更多是工具型公司。但是大家今年都在弄场景落地,感觉你们对于落地各个场景这件事上,好像会审慎一些?
张巍:不,我们也做,不过做的方式是和我们的IDS一起做。我们是没这个Know-how去进场景。可以说,我们比大多数机器人公司,退了一步。
在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,我们卡位底层平台,提供本体、小脑、模型开发工具链,对应的是iPhone、iOS、Xcode,帮助我们的客户开发把机器人用起来的APP,不同的APP完成不同的任务,把开发者生态培养起来,赋能千行百业。
做机器人,别直接照搬自动驾驶
《智能涌现》:现在机器人行业对于数据重要性的看法也并未达成一致,有的人认为应该在模型确定后再堆数据,有的人认为没有数据就不可能产生好的机器人模型。您对于数据的判断是什么?
张巍:我对于数据的判断是,假如数据足够多,不用争论什么端到端,机器人什么任务都能做。但问题是:这个“如果”不成立。
《智能涌现》:这里的数据,指的是真机数据吗?
张巍:是有价值的数据。
《智能涌现》:感觉你们好像不太强调真机数据,反而更关注仿真数据?
张巍:在真机上去做强化学习,是最近比较重要的技术进展。自动驾驶就是相对简单的具身智能。自动驾驶领域有上千万辆车在收集数据,这么多公司、这么多长时间收的数据,还是L2++++。
自动驾驶是收集数据的典范,有部分人是从那个自动驾驶思维跳过来的,但机器人不能直接 copy,因为机器人不是一个A到B的问题,真机收集数据的话,得雇这么多少人?用多长时间?我觉得太笨了。
现在有很多数采工厂,建一半都不想建了,因为不知道这个数据给谁,那就先建着呗。大家都是将信将疑的往前做。
我觉得真机数据非常重要,这个重要性没有任何分歧,但是它不是未来机器人落地的变量。从成本上讲,我们希望找到的技术变量是,不需要这么多真机数据。变量在哪?就是仿真数据和互联网视频数据。我希望找到的是能够高效使用数据的方法。
《智能涌现》:你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要解决数据效率问题,需要把「工业母机」做出来,它具体怎么理解?
张巍:具身智能的核心挑战,其实就是如何在数据上降维打击,找到更低成本、更高效率的生产模型的路径。所有算法上的突破,本质上都要回到一件事——降低数据的成本。
我现在关注的不仅是模型能做什么,而是如何让模型以更快的速度、更低的代价被生产出来。我把这比喻为生产具身模型的“工业母机”。
它的核心任务是把数据转化为模型,现在某个模型的性能跑得好不好不重要,我不着急做一个模型、去打榜,而是看能不能高效、低成本地持续生产模型。
在数据上,你不能指望靠堆真机数据去开发模型,那样效率太低。开发具身大脑技术,数据本身不是本质,本质是数据背后的信息。未来潜在的低成本、高效的数据来源,一个是仿真数据,一个是视频数据。这其实是“工业母机”提高效率的最大突破口。
《智能涌现》:有的公司对数据有要求,比如要达到多少小时,数量如何等等。您对于机器人数据具体的标准是什么?
张巍:我们有一个不纠结的东西,我们没有对立数据和传统的模型,我觉得模型是数据的一种蒸馏和抽象。
我的关注点是,机器人公司有没有把视频数据用起来的能力。如果你没这能力,只会堆数据的次方,那大家都会堆,差异只是有的只能用第一视角,有的用第三视角,还有的是多视角等等。堆真机数据的要求就更低了。谁能巧妙地把这事干了,这才是我关心的。
封面来源|IC photo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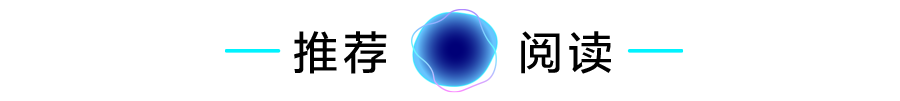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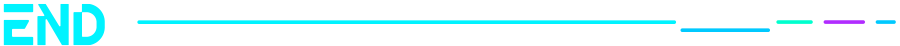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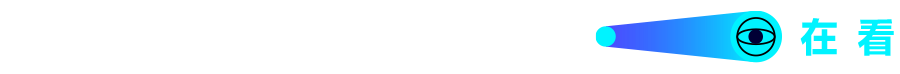
(文:智能涌现)

